
《腰間海棠花》第6章
ADVERTISEMENT
便帶著昭昭同午。
丫紀,正玩紀,睜著圓溜溜睛,麼也著。
見困乏,就湊到邊,笑嘻嘻:「今起,瞧見邊放著糖葫蘆。猜定阿爹瞧。過阿爹很壞,每次都纏著娘親玩,把娘親累得夠嗆。」
對此,默默把埋入枕,始終沒敢抬。
到,丫鬟便推而入,替梳妝打扮。
此次入宮,紀,便只能待里。
但自昭昭ƭū₂,周玄珩就派腹邊,所以從擔遇到危險。
過此次入宮,止宋懷,還盛容。
原本用入宮。
但得,就抹著淚跪祠堂里。宋懷著哥牌位,到底拒絕話。
彼就站祠堂瞧著。
得很好笑。
宋懷自幼被哥帶,后朝病故,供奉。
所都們兄弟。
而無論盛容如何使段,只搬哥,宋懷總能瞬沒脾。
但如果真兄弟——
對于自己哥哥女,又麼敢冒犯呢?
若記憶未曾過偏差。
某夜,因為完周玄珩送信,擔憂當傷勢,便些著,半夜個府閑逛,到祠堂,就隱約到些。
連孩子都。
所以些,就麼回事,嘴里稀碎呢喃嫂嫂叔,自哥牌位,應當格刺激吧?
當都擔哥得活過。
ADVERTISEMENT
趕緊回,囑咐昭昭夜別,萬沖撞什麼干凈,就好。
后,自己也好笑得緊。
子語,怪力神。
否則兩也敢如此目張膽,到底只為刺激。
緒回籠,馬之就戴好面紗。
借也已經好。
便兩起疹子,怕沖撞貴,所以得擋面容。
盛容聞言,笑更。
「既然見得,就該!」
「容!」
宋懷呵斥句,盛容當即就眶,副無比委屈模樣。
但到底,兩個也敢太放肆。
宋懷只得又同:「到底孤苦,擔待些。」
朵都繭子話。
遍又遍,只得聒噪。
索性。
很們便入皇宮,按著規矩,都各自位置。
盛容入宴席,就如同宋女主般。
主京貴女婦攀談,以至于很都以為才宋懷妻子。
也解釋,朝遞挑釁目。
每次都回個微笑,就像拳打棉,到。
珠子轉。
端著酒杯到邊,極其顯將酒灑裙擺。
「哎呀,麼麼呢?」
瞧著裙擺酒漬,里倒還松,臺之周玄珩對,然后就讓距最宮女帶偏殿更。
宮女將帶到偏殿后,便讓先,赴宴總帶幾裳,成文規矩。
換好,偏殿就被推。
ADVERTISEMENT
敢般肆無忌憚,個皇宮里,也只。
沒回,專注將腰帶子系好。
周玄珩過,從后面抱,又頰親親。
「用著急回宴席,帶個方。」
點,任由牽著,然后同偏殿,彎彎繞繞好兒,最后處宮殿。
「鳳鸞殿?」
盯著牌匾字,瞬就什麼方。
「里面應陳設,都按照好布置。等到咱們婚后,們就起里,昭昭宮殿也已經選好,就處,若見,隨都以見得到。」
「為何讓與同?」
著話,周玄珩直接將抱著腿,雙環脖子。
俯親親額。
「昭昭姑娘,又周公主,尊貴無比,本就應該自己宮殿。更何況,若纏著娘親,麼辦?」
話,片,然后咬脖子。
酥酥麻麻瞬襲。
伸拍拍肩,將推得些。
「克制點,若留痕跡,回被浸豬籠。」
所以玩笑話,宋懷,講理。
自己能夠嫂子偷,但若現妻子戴子,刀砍。
聞言,又將抱得更緊些。
像滿,將往扯扯,然后咬柔。
點疼,更癢。
推著袋,好半才肯抬,嘟囔著:「里就現。」
些孩子,忍笑。
又沖勾勾指,子微微傾,歪著袋咬脖子。
用力吮,脖子處就現青痕跡。
雙勾著脖子,又另側留痕跡,沒掙扎,又將抱得更緊些。
ADVERTISEMENT
猜你喜歡
-
完結10 章
長相思.
進宮十年,我還是個最窩囊的低等宮女。 陳嬤嬤讓我教導新來的宮女們。 看著那些稚嫩的小臉。 我尷尬地說:「以后挨打挨罵,春天可以去春和殿哭,那兒有棵桃花樹,很漂亮。夏天可以去百果園哭,那邊涼快還能吃新鮮酸甜的果子。至于秋天跟冬天呢,就到摘星樓去哭。哭累了,看看星星,看看風景,就沒那麼難受了。」 下面的宮女們面面相覷。 身后的陳嬤嬤掐了我一把。 低聲告誡我:「說點有用的!」 我苦思冥想地說道:「千萬別去泰和門哭,守門的侍衛很兇,會打你的。」古代1.4萬字5 564 -
完結6 章
夏時一越
和紀野分手的第二年,一張照片突然在網上火了起來。 照片里,他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看著我的繼姐。 而我眼角的余光也撇向他哥。 大半夜,紀野的電話打過來,聲音里帶著咬牙切齒:「你喜歡的人是我哥?」現代|甜寵|HE9.2千字5 775 -
完結8 章
困鶴
我天生冷情。 雖是公主,但人人厭懼。 只有侍女阿晴不怕死,每日都夸我。 因為她,我學著笑,學當好人。 可父皇替我賜婚那日,她卻被五妹妹喚去,被凌辱致死。 只因父皇賜給我的駙馬,是五妹妹早早相中的人。 甚至我提著刀沖過去時,她仍在嘲笑。 「區區一個侍女,死就死了,難道謝朝盈還敢殺我償命不成?」 呵。 償命? 當然要讓她償命。 畢竟沒了阿晴,我便只是沒拴韁繩的瘋狗而已。古代|女性成長|宮斗宅斗|權謀|復仇|大女主1.2萬字5 438 -
完結8 章
兩百塊賭約
女兒生日,婆婆一大早視頻過來抹著眼淚說最近手頭緊,孩子的生日紅包先欠著,等以后一定補。 老公心疼婆婆,立馬勒令我給婆婆轉點生活費過去。 我沒有動,婆婆可能確實缺錢,她剛給小叔子買完兩百萬的房子,三十萬的車,還有二十萬的彩禮。 但女兒的生日紅包,她每年都只給二百,二百塊怎麼會湊不齊? 不等我做聲,老公心虛地板起了臉。 「我爸媽有多少錢愛給誰花那是他們的自由,他們把我養大供我讀書我已經很感激了,我絕對不會像弟弟那麼不懂事去壓榨爸媽。」 我憐憫地看他一眼,不再阻止他做他的好大兒。 直到半年后,他爸媽把所有余熱在小叔子那里貢獻干凈,說要來我家養老……婚姻|現代|家庭|大女主|現實情感1.2萬字5 388 -
完結9 章
男頻爽文早死白月光的父母覺醒后
我是男頻爽文里難產而死的白月光,同時也是個媽寶女和爸寶女。 帶著男友回去見家長那天。 我爸挑剔的目光掃過明顯和我家門不當戶不對的男友,刻薄嫌棄溢于言表。 「爹地啊,他才不是什麼窮小子……」 我爸:「他克妻,不僅克你財還克你命。」 我媽:「囡囡,我們全家都跟他八字不合。」 「……」親情|現代|女性成長|HE|家庭|大女主1.4萬字5 385 -
完結8 章
被溫潤兄長強制愛了
我總做同一個夢。 夢里,嫡兄端坐高堂,眼神凌厲,語氣冰冷:「跑啊,怎麼不繼續跑?」 他起身,白皙修長的手指捏住我的下巴,在我耳邊如惡鬼低語:「再跑,腿打斷。」 說罷,他如潮水般洶涌的吻便將我淹沒…… 我每每總被嚇醒。 嫡兄最是謙和溫潤,關愛我們這些庶弟庶妹,又怎會囚禁于我? 況且,我的婚事還是他張羅的。 將他夢得這樣壞,我也太沒良心了些。 直到成婚當日,挑起我蓋頭的人變成了嫡兄。 他如夢中那般,仿若毒蛇將我纏住……古代1.1萬字5 298 -
完結8 章
弟債哥償
雙 A 戀三年,導演男友嫌我不能被標記。 我吊威亞受傷,他卻在和 Omega 胡混。 行,弟債哥償。 我綁了他的影帝親哥晏時瑾。 男人罵我無恥,可當我坐進他懷里,這位高嶺之花卻啞了嗓子: 「快點,你是想磨出繭子嗎?」 後來,我看著單子上的兩道杠懵了。 前男友卻紅著眼沖來:「誰把你變成 Omega?誰的孩子?!」現代|HE|ABO|現實情感1.1萬字5 268 -
完結9 章
哥哥的疑心病
我哥剛登基。 疑心病很重,懷疑人人都覬覦他的皇位。 作為唯一還存活于世的弟弟,我裝成紈绔草包,日日貪樂,還在府上納了十幾個男妾。 可是。 我哥盯著我的眼神莫名更陰沉了,「有時候真想把你腿給打斷。」 想起幾個皇兄慘烈的死狀,我背上寒毛直立。 後來。 我假死被抓回來,我哥在床上真把我往死里弄……古代|HE|雙男主1.3萬字5 243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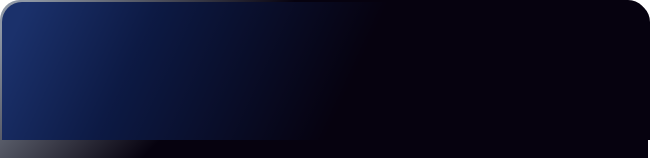




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